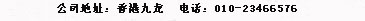凯里乡村月光下的夜生活,可惜现在已很难见
明月之夜(图片来自网络)
凯里乡村曾盛行一种古朴浪漫的夜生活堪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可惜现在已很难见到天上挂着一轮明月,明月下的村庄非常热闹,有的人在织布、打毛衣,有的在吹牛聊天,还有的在约会,小孩子们则在玩躲猫猫的游戏……这样的场景比不上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但也是够令人向往的了,这是进入本世纪之前,凯里乡村“夜生活”的真实写照。那时候,只要天上有明月或者说天气不太坏,人们吃过晚饭,就会走出家门。年纪大的、已婚的聚集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做点事情,比如织布,打毛衣,补衣服……小孩们在操场坝玩游戏……大家忙活到深夜11点,才逐渐睡去。
我们寨子曾经有一个妇女歌队,她们利用晚上的时间聚集在歌师家门口,练唱山歌、酒歌,唱得太投入,到次日两三点才散去,二、三公里外的村寨,都能听到她们美妙的歌声。夜生活的安排也会随着时令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比如在插秧的时节,人们还会趁着有月光的好天气,背着自制的弓箭,到田野里去抓泥鳅和黄鳝,忙活到深夜,收获几斤,回到家煮食之后,才睡去。
又比如在“七月半”过“鬼节”期间,只要是明月之夜,村里老老少少都要出动,点香烧纸放“七姑娘”(一种神秘的活动)。
最有意思的是未婚青年们,皎洁的月光主要为他们准备,其中的男性将离开家,到别的寨子去,去做什么呢?找心仪的人,在我的家乡,叫“闹姑娘”或“玩姑娘”。那时,没有手机,就吹口哨,如果之前有约,听到口哨,女方会偷偷走出家门来约会。若男女青年之间之前没有任何感情基础,那难度就要大些,吹口哨可能没效果,这样的情况,胆大的男青年会选择上门去做客。上门做客,必须规规矩矩,若引起了女方家人的反感,轻则被请出,重就要挨揍。也有的先被礼貌请出,却在半路挨揍的。如果对来访的青年小伙有好感,女方的家人们会走开,把时间和空间给年轻人们腾出来。接下来就看小伙的表现了,如果女方有那方面的意思,她可能会和他走出享受月光,进一步发展;否则的话,对小伙就是一种考验了,至少是口才上的考虑,嘴巴不太会说的,经常灰溜溜的走出女方家,然后郁闷返家。还有一种情况,一起去女方家的,是一群男青年(女方有时也会喊来同伴助阵)这就存在竞争了,谁最终能把女方(或她的同伴)喊出去,谁就是赢家,当然,决定胜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长相、口才、口碑,以及家庭经济条件等等。
明月之夜景美如画(图片来自网络)
我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闹姑娘”的事,去过两次,但运气不好,姑娘没闹上,还惹出了麻烦。一次是随堂弟去了7、8公里外的一个山寨,他的女友在这个寨子里,我除了“陪相公”,还想去碰运气。当天月光很好,堂弟如愿见到了女友,不料后来被“冤家”撞见,在寨子里追打起来,动静不小,我们只得撤离。还有一次,我和几位初中同学抱着“闹姑娘”的想法去了与黄平县接边的一个寨子,同学们都分别和当地的女孩聊上了,只有我“搞不倒事”,原因说起来很好笑,都是鼻梁上的眼镜太不接“地气”。
我主动接近的女孩说:“你是做什么的,戴个眼镜?”说着,就慢慢的走开了——在她眼里,我就是来路不明的“另类”,如此,别人只有敬而远之了。接下来,也是因为眼镜,出了事情。我主动接近的女孩刚走,当地的几名青年小伙就出现了,看到了站在路边的我,他们靠近,并拿我鼻梁上的眼镜借题发挥:“戴什么眼镜,我看你有点冲。”我是外村人,自然不敢答话,对方却不依不饶,走出一人封起了我的衣领。同学们闻讯赶来,差点与对方干了起来,但最终选择了退让。在回去的路上,家就在当地的同学海告诉我,闹事的小伙与他之前有点过节,眼镜不过是导火索而已,矛盾之前已埋下。后来,因为读书求学,我逐渐远离了家乡,也远离了这种“明月时代”的夜生活。多年后,当我返回家乡工作时,发现这样的生活图景,已经远去,每个村寨,夜里静悄悄的,月光也变得孤独。我怀念那个时代,但它的离去却是无法阻挡的必然。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下,有劳动力的人,也就是主宰“明月时代”的主体都进了城,村子就只留下了60岁以上的老爷爷老奶奶和乳臭未干的孩童。再者,手机成为了人们联系交流的重要载体,男女青年之间,已不用通过登门拜访的方式来认识、交流。而在网络世界认识,遂确立恋爱关系,甚至“终成眷属”的方式逐渐成为搭建友情关系和婚姻关系的主流。社会的发展,会让许许多多的生活方式走向终极,既然无法挽留,就把它珍藏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吧,它会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许会成为忙碌世界的调味品和静心剂。(凯里快报)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kailizx.com/klsmj/1962.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