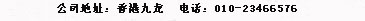凯里游思从娱神到娱人丨阿福行记
编丨陳九千
你是所有人,曾经在世或仍旧活着的,全部。
——AndyWeir
丨写在前面
对贵州的好奇与向往,源自几年前的一场偶遇。
几年前,我在广州出差,在一个过街天桥上,看到一个留着长发和胡子的诗人,在摆地摊卖他的诗集《南往耶之墓》。出于好奇,我停下脚步与诗人攀谈,并买了一本他的诗集。
雷公山锦鸡苗人,南往耶
交谈过程中,我了解到:这位长发诗人名叫南往耶,来自贵州雷公山,苗族人。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雷公山这个地名,此前也只是坐火车的时候路过贵州,因此很难对它建立起具体的印象和认知。
与南往耶本人仅有的一次接触和交谈给我的印象,感觉他是一名狂狷之士。他跟我聊起雷公山的一些情况,聊起他的个人遭遇。他自信他是雷公山近几百年以来诞生的最有才华的诗人,并自诩为盛世的斗士;但天妒英才,他总是遭到政府和当地恶霸势力的打击跟迫害。
这自然是他的一面之词,我无从证实,也懒得证实。天气很热,我们都很焦躁。买了诗集之后,便与他道别,忙我自己的事情去了。
但,与“南往耶”的缘分却并不止于过街天桥;至少,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闽粤地带,在觥筹交错、和光同尘的名利场,他的狂傲,以及表现出来的一个斗士的姿态——无论是作为一种表演还是他真的想战斗,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南往耶之墓》是一本现代诗集,大概率是作者筹资或自费出版的。
翻开诗集的封面,里面有一张年轻裸女的彩色照片。她长发及腰,一丝不挂地坐在城市高楼的落地窗前,窗外的斜阳打在她晶莹透亮的胴体上;高耸的乳房被阳光染成了金黄色,分外迷人。
南往耶自己的注解说,这位模特是他的一位苗族姐姐。他盛赞天地造化,孕育了这位苗族姐姐的美、自信和性感。在他心里,她的形象,几乎成了雷公山一带苗人的化身和集体写照。
我无法以一个文学评论员的身份去评论一本现代诗集的文学水平,但我确实很认真地读过里面的每一首诗,有些还摘抄在我的读书笔记里。
这是一本民族意识和主体意识都很强的诗集,里面描写了很多关于雷公山的传说和传统,还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他的弟兄姐妹和父辈祖辈,以及他们在命运抉择中所表现出的彷徨和挣扎。
和大多数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民族群体一样,这种不顾一切地彰显自我的民族意识和主体意识,往往是在与“强大之物”相碰撞之后,才凸显出其剑拔弩张的态势。在雷公山和南往耶这里,他们所面对的无处不在的“强大之物”,一方面是公权力,另一方面是现代化进程。
从诗集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觉到作者对苗人传统的珍视、继承和留恋,以及他对亲人和族人的爱和爱莫能助;但最激烈的,仍是他对“强大之物”的对抗情绪,以及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鲁莽或豪气。
几年后,当我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和传统有了粗浅的了解后,我才隐约感觉出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大无畏”和复仇意志,有着上古时期蚩尤和共工的影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从南往耶和他的诗集中,我本能地联想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对鸡蛋和高墙的隐喻。这个隐喻的背后留下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要不要让脆弱的鸡蛋去撞击坚硬冰冷的高墙——这是对“猛志”和才华近乎愚蠢的浪费,而是,一颗蕴藏着无限可能的鸡蛋,如何飞跃这高墙!
丨印象凯里,多彩苗人
今年8月初,在湖南湘西的凤凰古城,看完“乡下人”沈从文的坟地和故居之后,坐长途大巴一路西行,进入贵州,抵达铜仁,正值中午。拖着行李瞎逛了一个小时,吃过午饭,便直奔高铁站,迫不及待地前往凯里。
傍晚时分,雨后初晴,夕阳斜照,高铁行驶在高原上,穿过零星分布的村落,像闯进了一幅画卷里。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贵州省基本都在云贵高原上。接下来的几天行程,无论是在高铁轨道还是在高速公路上看窗外的风景,全是连绵不断的山:山涧植被茂盛、千沟万壑;山顶则是草原牧场。
从铜仁到凯里的路程很近,一个多小时的高铁就到了。从凯里南站出来,已是暮色沉沉,我拖着行李走出车站,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到达市区。在朋友吴媛媛分享的地理位置附近,我订好一家旅馆,办理好入住,已经晚上8点多了。
吴媛媛是我在深圳工作时的前同事,这是个怀揣着编剧梦想的女孩。年轻的她,单纯、活泼、愿意尝试不同的新事物。我们相识于深圳的一个编剧培训班,后来也一起共事过一段时间。离开深圳后,她去了北京一家影视公司,从事文化和编剧工作。再后来,她回到了她的家乡凯里,在当地一家旅游开发公司工作。
第二天早上,她带我去当地一家生意很旺的早餐店吃酸汤砂锅粉。吃完早餐,我们一起去参观附近的民族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的主体建筑一共有三层,全称叫做中国民族博物馆黔东南分馆,着意呈现当地的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因此对历史通识的部分介绍相对较少,汉朝以后至明清阶段的历史通识,几乎没有。
凯里市的全称叫做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漫步于民族博物馆内,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凯里境内苗族、侗族、瑶族、布依族、水族、壮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沿革、生活习俗和服饰文化。
于我而言,在博物馆参观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填补了我对苗族的历史沿革的认知空白。此前,我只知道苗族、土家族和畲族等南方少数民族都属于蚩尤的后代,分属于九黎三苗;但却不知道,苗族其实是自东向西,从东部沿海迁徙到内陆贵州来的。
我也是来到贵州之后才了解到,整个苗族内部又有不同分支,可分为黑苗、白苗和花苗。岜沙苗寨中穿着黑色衣服,至今仍保留着用镰刀剃头这一风俗的族群,应该属于黑苗。而贵州西部、靠近云南昭通的毕节石门坎,普遍属于花苗。“花”亦指杂色的意思。
在服饰展览厅,印象深刻的是苗族和侗族的育婴带,那是母亲在出行和劳作时背婴儿用的。育婴带的中间很宽,两端修长,做工精细,绣了不同的花纹,表达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祝福。它们款式不一,挂在墙上,让人联想起女人的子宫和卵巢。
从博物馆出来,吴媛媛带我去逛古城老街的集市。她说:“你很幸运,今天刚好是周末,大家赶集的日子,可以看到当地最有特色的东西。”
她先带我去老街的菜市场,这片区域除了卖菜,还有当地的苗族老人摆摊卖山上采回来的草药,街边不时还能看到老太太用米粒和鸡蛋给人算命。
我问吴媛媛:“你找她们算过命吗?”她说,她父母给她求过姻缘。
从菜市场出来,她又带我去了服饰一条街。这条街上,全是不同款式的苗族服饰,美不胜收。扎着发髻的苗族妇女,在这里精挑细选、货比三家。
穿过琳琅满目的服饰一条街,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巷深处,吴媛媛又带我去银饰街。这条街上,被匠人们千锤百炼、精雕细琢的银饰,像地摊货一样摆在货柜上。眼看着这些雪白耀眼的银饰如此“不被待见”的样子,真心怀疑是不是假冒伪劣产品。柜台里,有些银链子还很粗大,挂在脖子上,感觉得有十几斤。
吴媛媛告诉我:“苗人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节日,逢年过节,都要穿着自己民族服饰,戴上这些银饰,聚在一起载歌载舞。所以,你在凯里看到的广场,都是圆形构造,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在节庆日跳舞。”
我问她:“你是苗族人吗?”
她说:“是啊。”
我又问:“那怎么不见你穿戴这些衣服和银饰?”
她说:“现在又不是过节。”
从银饰街的另一头出来,在十字路口的街边,一个卖苗人山歌和唱本的地摊,吸引了我的注意。唱本薄薄的,印刷略显粗糙,我却感觉很有意思,于是花5块钱买了两本。
逛完街已经快中午了,我们一起去吃血浆鸭。等饭上桌的间隙,我忍不住掏出山歌和唱本一睹为快,饭店的老板见我不像本地人,便端了一张小凳子坐在旁边,与我们攀谈起来。他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我是江西人。他说他的祖上以前也是江西人,我问他祖上是什么时候迁到贵州来的。他说他也不记得了,是当年作为犯人流放到这边的。
贵州地域在历史上被称为“夜郎古国”,因为这里曾经诞生过很辉煌的夜郎文化。从汉朝以后一直到明清这一千多年,贵州的大部分地区,都由当地的土司管辖,并形成了当地有名的四大土司家族。一直到雍正时期,清政府在云贵川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由中央委派官员到当地,中央王朝对贵州的有效管辖才更进一步。因此,贵州也长期被视为边陲“蛮夷烟瘴”之地,是古时中原政权发配或流放犯人的目的地。事实上,发配到贵州的犯人,有极大一部分还没到目的地,就因水土不服或传染病而客死他乡了。
丨下司归来,“高山水流”一场醉
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吴媛媛约上她的同事以及同事的男朋友,开车去距离凯里市区半小时车程的下司古镇,她们很想念古镇江边的蓝莓冰粉。
下司古镇位于清水江畔,在明清时期为当地的商埠重镇。据官方的史料记载,清水江流域,因其独特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宜林木生长,明朝正德年间,朝廷修乾清宫、坤宁宫,层层派出要员到湖广、川、黔等省征集皇木。明清两朝,朝廷在清水江边的锦屏开设“木市”、广证“皇木”,“民木商”随之大量涌入,木材贸易空前繁荣。
木材贸易的繁荣,孕育了清水江辉煌的木材时代,加速了下游封建商品经济和汉文化沿着清水江推进,创造了清水江沿岸悠久的木商文化。
在这一趋势下,下司古镇的商品贸易也随之兴起,并因其便利的水陆码头而成为黔东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明清政府也专门在这里设置行政单位。到了清朝后期,木商由以前的散商发展为有组织的商帮。诸商帮建立会馆,坐地经营。一时间,下司镇商贾云集、马帮成群结队,商号、货栈、会馆、餐馆遍布街巷,彻夜营业,有“小上海”之称。
如今,随着现代交通和物流运输的发展,水运日渐式微,下司镇也渐渐淡去了货运码头和物资集散的功能。但它在长达几百年的商品贸易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人文遗迹,却构成了西南地区与中原的互动与融合的共同记忆。这份共同记忆与历史遗产,也在现代社会演变成了宝贵的旅游资源,成为新的文化聚集地。
现在,留给下司古镇的一个问题便是:丧失了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之后的历史遗产,还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吗?它会不会最终成为一座空中楼阁,在风雨侵蚀中渐渐被遗忘?毕竟,文化也要遵循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
在江边的饮品店喝完蓝莓冰粉,我们便在古巷中信步闲游,却无意间邂逅了阳明书院。在贵州的文化记忆中,经常为人所称道的,便是遭贬官的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故事了。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开始在贵州传播阳明心学,三年间门人广布黔中;后在贵州阳明后学的努力下,经过多年的经营,最终形成黔中王门,出现了“贵州王学三先生”,其中以阳明再传之卓越弟子孙应鳌为集大成者。位于下司镇的阳明书院,便是孙应鳌等后学在贵州传播阳明心学的历史见证。
如今,这座古色古香的庭院建筑已经不再具有开课传道的功能,而被改造成了展示阳明心学内涵和主旨的展览馆,供游客参观。
回看历史,集中国传统思想之大成的王阳明,其所创立的心学,在东方思想文化史中的地位,并不亚于欧洲的宗教改革。细细品味,它们亦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
首先,在当时,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以儒学正宗为基础的阳明心学,摆脱当时盛行的程朱理学的窠臼,另辟蹊径,强调“知行合一”,顺应时代需求,开创了儒家学说的新境界。而欧洲的宗教改革,也在理论和组织层面修正了基督教义中日渐教条和禁锢的部分,放宽了教义的自由度。
其次,它们都扩大了其思想和理论的群众基础。阳明心学中的“人人皆有良知”、“人人皆可为圣人”的立场和开放度,使得儒学文化进一步向庶族平民乃至未受礼教熏习的“蛮夷”下沉和开放。而欧洲的宗教改革,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顺应时代的需要,打破天主教的精神束缚,吸收更多的教众。
但令人遗憾的是,欧洲的宗教改革极大了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的阳明心学,却没能在当时孕育出一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社会运动。
从阳明书院出来,我们又游荡到大码头、禹王宫(两湖会馆)和芦笙广场,感受下司古镇当年蛮汉交融的繁华与热闹。
傍晚时分,一行人驱车回凯里。回到凯里,已接近晚饭时间。吴媛媛说:“来贵州一定要有美酒,今晚你要不醉不归。”
她和她的同事好友带我品尝当地有名的牛肉酸汤火锅。这是一家颇具苗族特色的餐厅,餐厅门口,摆着苗人自酿的米酒,男子吹芦笙,女子唱苗歌,进来用餐顾客都要接过苗家女子的牛角杯,在芦笙和祝酒歌中,一饮而尽,热情洋溢。
在餐桌上,认识了吴媛媛的本地朋友龙江桥大哥,与他聊起我对贵州的最初想象,以及在广州和南往耶和雷公山的那场“偶遇”。
没想到,他竟然认识南往耶。“你说南往耶啊,他在凯里挺有名的。他最近才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头发和胡子都剃了。雷公山距离凯里很近的,不过开车只能到山脚下,得徒步才能上去。”
我说:“感觉南往耶这个人挺狂的。”
他附和道:“嗯,是挺狂的。”
随后,龙大哥又把南往耶最近的照片和
转载请注明:http://www.kailizx.com/klsrk/8473.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