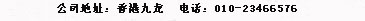张冠仁那些渴望被承认被重视被拯救的
文
张冠仁
我始终有一个比较偏激的观点,对于有才华和野心的新导演而言,在处女作中将自我风格极致化表达是有一种天然的合法性的。当然前提基于那风格化是他与生俱来而不是刻意伪装出来的。毕赣的长片处女作《路边野餐》令人惊喜,在短短分钟内,它至少做到了浓郁的混血个人风格表达,强烈的去中心化文化和自觉去类型化的三个维度。这对于一部文艺电影来讲,毫无疑问是具备高度自觉性,而且自成一路难得的少年老成。
▍混血的个人化表达年,毕赣的横空出世是相当令人意外的,尤其是夺得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之后,媒体发表的采访《我的电影是拍给野鬼和风》让人们先于电影知道了他。作为新人,他首先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母语语境:黔东南凯里。就像山东高密之于莫言,纽约之于E.B.怀特,马孔多小镇之于马尔克斯一样,那是他如鱼得水的地方,也是新导演孕育的温床。许多曾经的新导演最初也会遵循这个方法论去寻找自己的创作母语语境,比如曾经的汾阳之于贾樟柯。《小武》、《站台》里的汾阳让全世界惊叹:原来自年中国社会开启了“城市化”进程之后,还能在电影里看见一个如此清晰地保留甚至还原了“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小人物与空间的样本:崔明亮(王宏伟)和尹瑞娟(赵涛)还有张军(梁景东)是如此鲜活而真实。可惜十几年之后,人们在《山河故人》中看到了人到中年疲惫不堪的赵涛,飞驰而来拍马赶到的梁景东。他们依然能够努力地还原起过去时空,但是在构架起通往未来的努力时,那座桥却过于轻盈而并不可信。当然关于未来性的架构没有现实依据可以参考,所以对创作者而言是最难的。毕赣在《路边野餐》开宗明义引用的《金刚经》也是三个时空论:“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些是毕赣无法用语言理性阐述的感受与体悟,所以他才会选择用影像来表达。他这次主要处理了过去与现实二元时空,当然他聪明地玩了一个小花招,用侄子卫卫同名梗来隔山打牛暗示了时空未来的某种可能性,但总体而言,《路边野餐》其实是一部关于如何在时间中旅行的公路片,它要设置的主场位于过去与现在。
但他又超越了这一点,他把自己的据点进行了个人化的改造,于是凯里成了他的“荡麦”,一个充满了各种可能与成长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又紧密系扣在这个27岁年轻导演身上的创作母语语境。从视听语言的语法师承上,毕赣是杂糅且独特的,带有混血的特质:有塔科夫斯基的基调,也有安哲罗普洛斯的凝视,当然少不了侯孝贤的气质,这种血统混杂的风格在新导演身上并不少见,难的却是融会贯通,能叠化成自己的影像风格。这一点恰恰是毕赣独特性之所在。在影像的节奏上,《路边野餐》是舒缓,却又不慢,在杂糅复杂的镜头中有着一种不常见的节奏感,不疾不徐。大量写意抒情性场景和片段,并不承担叙事功能,镜头不重于判断,而只是在静默中呈现,重在营造独特却又让观众能沉浸入内的诗性空间。因为每一个镜头急着要给观众答案那是类型电影的路子:一场加一场,水泥搭墙的结构,就担心功能性不为观众接受。但是一部以自我表达为要务的电影,并不是必须给观众一个明确的信号:看好了,这场戏要告诉我们……比如其中关于时间的道具化隐喻是清晰可见,那个钟是童年卫卫画的,他是时间制定者;而在荡麦中他穿越了时间成为了一个青年,陈升从荡麦归来之后,这个钟又被叠加在呼啸而过的绿皮火车上,再次成为了旅行的解码器;在结尾之前,陈升和家族长辈沟通,手表倒影明晃晃地出现在前景,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能指,指向一个清晰却又模糊的空间,也就是钟表为砖瓦,砌成了影像上的四堵墙,把毕赣需要的时间囚禁于内。
再比如说,出发之前,陈升经常出没于一个常年湿漉漉的人防地道中,这也是他个人困境和精神世界的外化,当他轰鸣上路之后,片名字幕才缓缓出现。黔东南是一个神奇的所在,作为苗族与汉族混血的毕赣,这片土地有着野人传说、巫师、乡野传说、诗歌、密咒、空间循环……换言之,他在一个五方杂处的空间里找到了处女作天然游乐场。而从电影中的歌曲来说,无论是李泰祥还是伍佰,大量出现的粤语歌曲也是90年代香港文化北上的具体表征。有一个挺有趣的细节,甚至在西藏拉萨八廓街听到粤语歌曲的感觉也不会让人觉得那么违和。这可能也是香港流行文化渗透性吧。
▍一个不愿意住在北京的导演毕赣还有一个让我惊讶的地方,他对自我创作的高度自觉性:集中体现在他拒绝生活在影视业资源集中地,北京。在一个连香港导演们都削尖脑袋想去北京“搞创作”的时代,这个山西毕业的贵州年轻人居然拒绝了帝都的召唤。他认为那里是创作的水泥之地,他宁愿在他自由自在的凯里呆着,不愿意去北京,这意味着他会失去多少“机会”和“灵感”么?很简单,除非必要,作为一个沟通成本极高的行业,没有一个制片人会优先考虑一个家住贵州的青年导演,如果他不是无可替代的话。北京的地理构架像极了整个中国,聚鼎一尊,以中央为首,以二环为核心,资源配比和房价渐次展开,以比五环多一环的六环为底。每一环的居住人群基本处于各自的社会阶层与社会鄙视链中,除了一些六环外豪华别墅人群不谈。基本上一旦发生冲突,以家住六环的朋友礼让二环的朋友为多数。没办法,这是百年以来权力格局造成的地理同构。离紫禁城越近意味着距离资源也近。在某种程度上,他就像20世纪早期那些想当作家的家伙拒绝了来自巴黎的邀请,非要蹲在美国南部当一个乡下汉子,是的,没错,我想说的就是威廉·福克纳,作为一个在当时难得认为巴黎并不构成对青年作家吸引力的人,他和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们分道扬镳。他只专注于邮票一样大的密西西比州约克纳帕塔法县,最后他成为当代美国文学史最无法绕开的作家。放弃与获得往往成正比,在失去机会的同时,他也因为这种“地缘劣势”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如果说贾樟柯更多是从社会结构性进入电影的话,或者反过来说,上一代中国电影人在完成影像表达的时候,中国的当下性既是财富也是包袱。我认为《山河故人》中暴露出来的疲态并不是专属于贾樟柯个人的悲伤,而是优秀创作者本体性和时代性如何共处的问题,比如之前一代导演所拍摄出来,以文艺青年内心苦闷为叙事主体的电影《孔雀》、《立春》、《站台》等等。其中文艺青年的苦闷和所处于三四线城市的本体勾连在一起,他们同处于一种渴望被承认、渴望被来自于“大城市”重视和拯救的“可怜”模样。《立春》里王彩玲最具代表性。和这些急切得到外面世界认可的主人公不同,《路边野餐》展现出一种新内省式态度。作为一个写诗的医生,男主人公陈升最需要的并非是得到他人的认可,而是和自己往事达成和解。也正因为这个逻辑,《路边野餐》必须是以方言为表达核心的电影,方言和普通话构成了一种具备张力的对立关系,为了捍卫作品本身的本体性和坚持边缘化的审美态度。
▍赤脚步行者必须绕道而行当然,作为处女作作品,《路边野餐》也并不是完美无缺,比如其中本来应该留给演员的表演空间却过于依仗毕赣本人的诗句,作为非职业演员,陈永忠完成得相当出色了,但是那些青春期气息浓郁的诗句和他中年危机的年龄感还是产生了匹配上的裂缝之感。相对于视听语言的水准,毕赣的诗句经常有漂亮聪明令人眼前一亮的句子,但是整体性还是比较符合他年龄层次,风格隽秀灵气。而优秀经典诗歌是能承载痛苦感的,这个需要时间和经历,两者缺一不可。还有那个长镜头,因为涉及整个非理性时空的整体连贯性,他必须用一个连续不断的镜头来表现,那么这种视觉的奇观性是不是还有其他可能性来展现?可能某一种读解“荡麦”长镜头的可能性就是那压根就没有实际存在过,这是存在于哪一个晚上的梦中而已。而眼下,他有年轻,才华,勇气这三样武器,在当下洪荒时代的中国电影中能够呈现出再多一些异质化,个体表达的影像作品,这都足以让人兴奋。更何况他那个完成度非常高的42分钟长镜头,在这个长镜头里,他起码完成了超过60个人的场面调度,以及3公里以上的空间,而在视点上完成了三个人物的转换,这些能力和展现出来的审美都是罕见而弥足珍贵的。以至于我愿意以10部同期上映陈词滥调拼命咯吱观众却根本不好笑的电影来换取1部《路边野餐》这样具备相当审美水准的原创电影:一部尝试打破时间物理线性原则,意识中发生断裂的公路片。用《路边野餐》曾用名《惶然录》里的句子来总结:“生活的一切不过是一个梦,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所为,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所愿,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所知。”(佩索阿)当然,最重要的是年轻的毕赣懂得了当大水漫天之时,赤脚步行者必须绕道而行的智慧,对于一个青年导演这些就足够了。
(本文原标题:《永远不要靠得太近,这便是高贵》)
张冠仁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编剧。
让所有人都想掀桌子的底层中国
国产动画片的大野心
《老炮儿》里的90后为何如此欠收拾
·END·
大家∣思想流经之地白癜风有治疗好的吗北京治疗白癜风能根治
转载请注明:http://www.kailizx.com/klsxc/11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