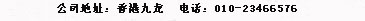看了路边野餐,我想吃着贵州牛肉粉念诗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号“Outrspac”(outrspac)。
《路边野餐》我看了三次。
3月26日,香港国际电影节。
7月3日,上海超前点映。
7月16日,上海影城。
至今仍然记得三月香港九龙湾星影汇放映厅内温度较低的冷气,无比清晰明亮的银幕,以及全程保持静音的观众。当然好的影院氛围对观影有好处,但记忆最深的还是《路边野餐》带给我的震撼。
首次观影前,我并不了解此片,也不了解导演毕赣,比如说他年生,双子座,这些一概不知。甚至不知道那场放映结束后导演会来到现场交流。
而恰恰是因为这些不知道不了解,才使我对这部电影保留了最纯粹也最原始的观感和体验,两小时不到的放映中几度屏息凝神,身处香港观赏这样一部大陆电影,有一种难以表达的骄傲和兴奋。
「凯里」
“山,是山的影子。狗,懒得进化。夏天,人的酶很固执,灵魂的酶像荷花。”
电影从开场便是导演所营造的儿时记忆里的贵州凯里,镜头下是南方山路边弥漫的湿气以及刚烧开的水要倒灌进热水瓶时蒸腾起的雾气,还有烟,还有薄暮,和昏暗闪烁的光。
“路边野餐”取自塔可夫斯基《潜行者》的原著科幻小说《路边野餐》。
电影中虚构的地名“荡麦”就像墨西哥小说《佩德罗·巴拉莫》里面的柯马拉一样。
香港那场放映结束后,有观众提问:“导演,我在你的电影中看到了娄烨甚至侯孝贤,请问你是不是把你的迷影情结带到了你的电影中?”
导演毕赣只回答了一句:“我不是一个影迷。”后来他又说过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任何一个导演他都只能给你一双鞋,路还是要你自己走。”
电影好看不是因为它像谁,而是因为它是谁。
我认为无论是塔可夫斯基还是侯孝贤,没有导演是不看电影就能拍电影的,可是对于毕赣来说,先前任何电影中的素材或表现方式就像“潜行者”一样进入他的潜意识,但电影最终还是完全属于毕赣自己的。它是《路边野餐》,更是《惶然录》。
可能是我观影量还不够多,也因为没有任何附加和累赘,于是我对此片有着初见般的纯粹。在现实、梦境、现实,在梦境般的现实与真实的梦境之间来回穿梭的体验如同一段奇妙的旅程,那种感觉同样很难用语言表达和形容。
「荡麦」
“荡麦的公路被熄火延长,风进入汽车后备箱。人类代替人类掌管家园,地狱颠覆地狱成为天堂。”
真正的“路边野餐”从此处开始,当然我也未曾计算过片名是从电影第几分钟才出现。
老陈从凯里前往镇远寻找侄子卫卫,袋子里装着诊所老医生给他的一张照片、一盘磁带还有一件花衬衫。
真正进入荡麦前,有一段几分钟的空镜长镜头,似乎是老陈与开车的司机的几段看似无意义的交谈。那个时候老陈坐在列车上,因此那些对话或者说是自言自语,就仿佛是在梦中又套置的一个梦,也有时间回到过去的体现。
对话结束,镜头回到列车上的老陈,梦境抵达最深处——荡麦。
途中偶遇在手上画着表的摩的司机卫卫,唱流行歌曲的青年乐队,将要去凯里当导游的洋洋,理发店的女老板……
镜头依靠这些人物的视线转换、推进以及延续,这些情节和对话又像套嵌的梦境和呓语。由一人到一人,搭建起完整的虚幻的路边荡麦。
洋洋听到火车开过的声音,老陈用手电筒照着理发店老板手指,虚拟出看到海豚的样子,更像是梦,也是向往。
老陈穿上花衬衫,唱完《小茉莉》,把那盘“告别”的磁带送给理发店为他洗头的女老板。
梦境戛然而止是导演要将故事停留在最好最沉醉的地方。
就像我们做梦,常被突然打断或惊醒,总是没有后续,而那段完整流淌的印象又总是回味无穷。
后来很多人对此片的评价,赞誉或者批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针对于“长镜头”。
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甚至没有想到要去寻找长镜头的痕迹,只是当列车像梦游一样穿梭时,我仿佛置身其中,追随镜头的轨迹,在铁轨和那个虚拟的空间中前进和游弋。
因为事先并不知道电影中有这样一个长镜头,也就不存在看表计算具体长度,不看他人的评价才可完全投入影片没有任何限制,于是那一次《路边野餐》给了我尤其好的体验。
很多电影都适合二刷三刷反复观看,因为每一次都能从中获得不同的信息和感受,但我始终认为电影的最佳观感一定是在第一次观看时。
你并不需要从别处搜集影片的信息,不需要刻意从影片中找到某种拍摄手法,更不需要知道“40分钟的长镜头”这样的关键词。
就像电影不该受制于形式和标准,好的电影不是它用了多少高难度的技法,而是它最终呈现的影像记忆是否完整流畅又能触动到内心某处;好的演员和观众也不源于专业;好的影评更不是撰写者的观影量以及经验之谈。
不过前几天二刷我还是计算了长镜头的时间,从电影第56分钟开始进入虚拟的“荡麦”,1小时37分左右结束梦醒,这个长镜头比较准确的时间在41点几分钟。但这是一次无意义的计算。
如果说首次观影犹如梦游般,那这一次计算镜头时间的观影显然比较清醒,坐在第一排也不觉得镜头太摇晃,但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观影方式。长镜头的时间本来就是无意义的,关键是它究竟为电影带来了什么。
后来在几次访谈中其实导演也提到:“它具体是40分钟还是60分钟都无所谓,我要的只是那一段完整的时间。”
「镇远」
“许多夜晚重叠,悄然形成黑暗。玫瑰吸收光芒,大地按捺清香。为了寻找你,我搬进鸟的眼睛,经常盯着路过的风。”
凯里和镇远是两个清晰的地方,这两段的叙述属于“现实”,而长镜头则完全属于导演虚构的地点和空间。
三个地点的时间和影像,中间是一段完整的时空,实则这个“长镜”并非长镜,而是段落镜头,它用于突显电影的结构,又完全嵌入影片中,也是无法独立的一部分。
梦的构成里,有往日记忆,有前日残念,对往后的期盼遐想,生活中的各种零碎的细节,各种感情关系,还有些胡思乱想。
当列车在床边穿梭,墙上车厢上画着的钟表快速转动,轨道的声响竟与时针的转动声有着奇妙的吻合。最妙的是梦的片段和诗的细碎给了我无比流畅的观感。
且不论电影的拍摄过程是断断续续的或是真正拍摄的时间要比举着摄像机排练的时间少出很多,又或者那段长镜头的拍摄用了多少台机器轮班交替,至少到最后它呈现出一段完整而且饱满的影像。其中有梦的缓冲,梦境深处还有梦醒时分。
手法和结构是值得探讨的一部分,但最重要的是影片给予观众的绝妙体验。而且你要是喜欢这个梦,你还能多看几遍,只是梦里的故事永远只会停留在那个地方,你可回味,也可想象。
电影的形式关于现实与梦境,剧情上则表达记忆与告别。台词与诗句,情节与场景之间,初看时的散漫零碎不知所云,到了二刷三刷以后就变得尤为明确清晰,错落之间相互关联。
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做梦、梦醒,回忆、告别。让“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以梦为分界线。
绿色车厢外画着的时钟转动,时间奇迹倒退,而现实什么都没有发生。却从一个孤独中年男人的自语和梦境来唤醒和忏悔,再通过“时间”这一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线索,构成了老陈的命运和人生。
失去母亲和妻子的老陈,梦中的绣花鞋沉入水底是与母亲告别;拿着诊所老医生的物件代替她与她的过去告别;荡麦偶遇的理发店老板又长着他妻子的样子;开摩的的卫卫和侄子卫卫都爱画钟表、谈野人。
过去的只能告别,往后的可以寻找。老陈寻找侄子卫卫的地方,就是真实存在的镇远。由此可见《路边野餐》中的地点、时间和结构的运用都非常重要,长而不断的梦当然很有必要。
在现实中回忆,在梦境里告别。有故事,才能写诗,有追忆,梦才丰盛。
诗作为一种意象的表达却未将电影剪成碎片,它仍给了我一段完整的奇幻的记忆,梦镜和现实的衔接也如同自然清醒般流畅。
但要问其意义,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它不为了表达某种具体的故事,却用难得一见的方式为你描述一段关于时间与记忆的梦境。诗词与影像相融流动,在虚幻真实,具象意象中穿梭流畅。
南方山区的气候,影像的主色调以及潜意识的深入,也始终给人以清新空灵之感,各种手持和后期,以及错落的诗句和重叠的镜像反倒不觉腻味。地域和方言更是极具魅力的存在,也是导演赋予此片的意义之一,似乎没有任何一种方式可以取代它们。
如果说第一次观看是沉迷在如梦似幻中如同梦游般兴奋,第二次是在清醒地计算镜头时间,第三次则是完全投身轨道中将剧情脉络梳理得更加清晰,看懂了更多细节的用意,听到了更丰富的环境声,看出了明显的瑕疵缺陷和不完美,但却更加喜欢。
这一次几度潸然,老陈的诗句念白,理发店里对着镜子忏悔,还有那首跑调的《小茉莉》,鼻子一酸就很想流泪。
不看《路边野餐》可能不知道,原来电影还可以是这样的。
看完以后最想做的事估计就是听着贵州方言念毕赣的诗,去凯里走一走,沿着蜿蜒山路进入荡麦路边,再放一曲《小茉莉》。
毕赣讲故事的方式不依赖于剧本,也不依靠台词,所有的引申和延续都通过镜头影像来完成。
虽然相对晦涩难懂,却就成就了他“有时令人费解,刻刻令人着迷”的作品。其实不必纠结于某处细节的用意,或是某个形象人物究竟是指代什么,电影是梦,也是我们不了解的凯里,是属于个人的私人的记忆。
可是对我而言,我看到的是粗糙镜头下,喘息的湿热的地域与方言,以及鲜活的自然的生命和景象。
第一次看完后就有为这部电影写点东西的想法,二刷后终于写下它,三刷后又陆续修改补充了好几个段落。因为我始终认为这样的电影应该多看几遍才能写出最完整的文字,但我不称它为影评。
就像导演说过,当你想要批评一部电影,首先应该看完它。
毕赣的雨,可以多淋几次,反正我,不爱撑伞。
“深圳文艺复兴”为头条号官方签约自媒体,精心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授权请
转载请注明:http://www.kailizx.com/klsmj/104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