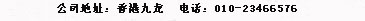一位89年出生的中国导演如何拍出一部惊艳
广获赞誉的艺术电影《路边野餐》昨日正式上映,中国青年导演毕赣凭借这部长片处女作斩获金马奖最佳新人导演、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以及多个国际电影节奖项,成为过去一年里华语电影的一匹文艺片黑马。
一群素人演员,拍摄前期只凑了20万经费,89年出生的毕赣结合诗歌、音乐和方言,用《路边野餐》讲述了一个在故乡发生的故事。《电影手册》甚至评价:「毕赣的出现,让贾樟柯后继有人。」但在影评人magasa看来,毕赣的这部电影让中国的艺术电影终于摆脱了历史性和社会性,和贾樟柯那种书写中国的野心不一样,毕赣的野心也很大,但完全是艺术性的,这让欧洲人觉得亲切。
文
刘璐
《路边野餐》导演
并凭借其获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
当再有个人问起毕赣曾经说过的那句「我的电影就像一场大雨」时,毕赣开始调侃地道,那句话是自己在印度的时候随便说的。这句话被放在《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各种媒体的引用中,后半句是:「但你们不要带伞」。
他当时当然是认真说的,但说过的话被解读一百遍后,毕赣就变得叛逆了。他回答了「一千九百遍」关于拍摄42分钟长镜头的想法,或者「两千八百遍」如何和非职业演员进行沟通的问题,以至于在狭小的汽车后座,他终于说出:「就把观众媒体当成像有帕金森的病人一样,他问我我讲一遍,他又忘记了我又讲一遍,说明我还是挺爱护他们的。」
在一天内跑完四场放映之后,他满脑子只想着打乒乓球。
叛逆是一种本能,除以上之外,他也对自己叛逆,影响比较深刻的一次是因为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潜行者》(这对毕赣来说又是一个讲了太多次的故事)。无所事事的大学生活,他看年的苏联电影《潜行者》,分了好几次才看完。最初,他带着某种常识的惯性觉得自己应该讨厌这种电影,决定看完之后写一篇影评来批判它。之后,在食堂吃着盖浇饭时,他恍然大悟自己早已经在观影的后半程里爱上这部电影了,并无条件地接受了它。从那以后,他把对《潜行者》的所有影评都变成了自己漫长的电影,所有拍的戏都在跟当时的美感对话。
毕赣已经想不起是什么缘由让他想要拍《路边野餐》这部让他拿奖拿到手软的片子了。「渊源和灵感对于一部作品的创作来说,从来都不是一次性的,它是由无数『一千零一个灵感』组合出来的」,他从年开始写这个剧本,一直找不到投资,年的时候,老师丁建国给了他几万块钱,妈妈和太太又一起拿了一点钱。有人问起拍摄期间的困难,他其实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资金、没有专业技术,他其实是无时无刻不在绝境中的。
在《路边野餐》的拍摄结尾,只剩下他和太太、录音师以及文学策划,他们几个人要补拍30%的内容,非常辛苦。但恰好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受到了一种状态,特别自由、毫无拘束、不用管任何人,一切都很顺利。
《路边野餐》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讲的是中年医生陈升带着一张照片、一件衬衣、一张磁带,从凯里出发去一个叫镇远的地方,帮另一位孤独的老医生把这些东西交给她的旧情人的故事,中途陈升来到了一个叫「荡麦」的地方。
毕赣去问一个苗族的朋友苗语里有没有一个表达「隐秘」的词,朋友告诉他是「荡麦」,他就用了,过了一两年,真正苗语专业的人却告诉他苗语里根本没有这个词。
毕赣从大学写剧本时就希望能建构出这样一个地方来——它是特别有趣,特别神秘的,有点像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里的科马拉。《佩德罗·巴拉莫》是毕赣认为自己需要反复阅读的唯一一本小说,这部被加西亚马尔克斯倒背如流的小说,在他写作进了一条死胡同的时候,解放了他,也在毕赣的阅读体验里成为最心有灵犀的一部。
鲁尔福用梦的逻辑在书写,毕赣也用类似的手法拍摄他的「荡麦」。相似之处在于,他们似乎是把这个地方的时间和空间先按线性排序,再用剪刀剪断其中的连接点,打乱顺序,重新来过。在荡麦,时间是非线性的,泯灭生死,恍兮惚兮的。
毕赣用明显的电影语言将电影里的三个地方区隔开来。在凯里,镜头做了一些圆周运动;在荡麦,是那个42分钟的长镜头;在镇远,则全部是固定镜头。分别是从县城、到乡镇再到纯粹的乡村。毕赣说:「电影是让我变成科学家,去探索时间是什么样子的,去追忆以前的记忆是什么样子的,可以带上幻想。」
时间是什么样子的?对毕赣来说(说了「一千九百遍」):「时间就好像一只隐形的鸟,我能看见它,但我怎么样让大家也能看见它。我需要一个笼子,把它关起来。这个笼子就是连续的、完整的时间和空间,就是那个长镜头。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还是看不到,我就需要一个梦幻的文本去给这只隐形的鸟涂上颜色,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它在里面是怎么转悠的。」
时间是什么样子的,父母离异让童年变得稍复杂一点,毕赣必须度过一些忍耐的时间。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诉说自己小时候的孤单,总是一个人,所以明显知道时间在那儿,而且他不得不忍受它。妈妈出去打工,他要忍受一年才能见到她,这一年对小孩子来说是漫长的。电影中的卫卫由毕赣同母异父的弟弟扮演(毕赣的小名也叫卫卫),他在墙上画了很多时钟,「时间也是可以具象的,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款式的表,也可以画上去」,毕赣说。
童年经历影响着毕赣思考问题的方式。小时候父母老打架,家里的灯老是因为电压不稳而闪个不停,这两者都让他不适。后来他把闪烁的灯这个元素放进电影里,却反倒让他有安全感。在荡麦的理发店,陈升和死去前妻的重逢地点,灯闪起来他才会有想法,先闪起来再说。
他似乎尝试在电影里帮自己解决童年时期的难题。和父亲同住的日子里,父亲有时候会把毕赣锁在家里,外婆从三公里以外的地方来看他,打不开门,在门外哭,最后只能哭着走回去。在电影中,卫卫却有一个会开锁的小姑爹陈升,每一次都能为卫卫开锁,不管是在潮湿的凯里,还是在梦幻的荡麦。
写诗的毕赣很在意节奏,在凯里,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血液里凯里的节奏可能就是人们在牌局上慢悠悠抽牌又猛地放下那个过程;而在瑞士,他第一次获奖的地方,人们的节奏可能就是游泳的节奏......这些都让他着迷。
所有的细节堆叠成了毕赣敏锐的感知体系,他会记得睡前妈妈讲了什么事情,爸爸上班前做了什么,奶奶身体的状况。很不幸他变成了一个创作者,这些细节就变成了他感受的比喻。
《路边野餐》这个名字和电影剧情关系不大,「我不希望观众受到文字的任何引导,而是慢慢进入电影的氛围之后,再得到某种提示」,毕赣将观影过程比喻成参观外婆家的房子,「你得进了大门,穿过院落,才在厅堂里看见祖先的牌位和祖训,你才知道,哦,这家人姓氏和来历,而在这之前的时间,你是通过对住宅的视觉体验来感受这家人的」。
陈升在荡麦遇见了过去和未来,为了让他不孤单,毕赣也为他书写了一个代表现在的人物洋洋。虽然片头《金刚经》里昭示着:「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但陈升还是把那盒本来带给别人的磁带送给了在荡麦遇见的逝去的妻子,这颇为浪漫诗意。
毕赣会用不同的语言来写诗,贵阳话、凯里话或镇远话,在电影里,陈升用凯里话念毕赣的诗。毕赣和贾樟柯不同,后者用方言来塑造人物,前者则是用方言来塑造诗意。
诗作为一个语言的媒体,被加入到影像的媒体中,代替了音乐来抒情。很多人告诉毕赣,电影的诗意不应该是文字的,应该是影像的,毕赣觉得这样把影像说得太高级了,影像是具体的东西,没有那么高级,真正的诗才是高级。他把两者组合起来。
在影评人magasa看来,毕赣的这部电影让中国的艺术电影终于摆脱了历史性和社会性,和贾樟柯那种书写中国的野心不一样,毕赣的野心也很大,但完全是艺术性的,这让欧洲人觉得亲切。
毕赣在国外拿奖,人们总喜欢问他从国际上学到了什么,他一如既往地叛逆:「我们太容易从国际上,什么都可以拿来吸收,其实电影不就是那么回事嘛,我在自己的家乡,我通过互联网,可以学习到拍电影的方法,学习到一些科技,我拍电影是去影响国际的,相反他来影响我的层面非常非常少。」
北京大学教授李洋认为《路边野餐》的诗的结构有一种神秘感,是中国特有的,并且与凯里的风貌息息相关。
毕赣在凯里生活了十多年,出去读了几年书,回来凯里就变了,中国的城市建设太迅速,这导致原本他剧本里的很多场景都被拆掉了。毕赣仍然在凯里生活,他觉得凯里在被建设以后,变成一个非常山寨的地方,总有人会在无意间把凯里与毕赣所谓的「故乡」相提并论,毕赣会敏锐又迅速地反对这种说法,「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说,每个人都会提故乡,我觉得特别地娇气,和矫情,因为我从来都在那边生活,也没有离开过……我当然很热爱这个地方,但它不是那种大家想得那么矫情的地方,不是对它饱含深情,充满热泪,不是这样的,那种热爱就是无缝得跟它连接在一起」。
毕赣也老在想故乡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塔可夫斯基寻找俄罗斯,结果发现曾经的很多东西都没落了。「不是在那个地方生活了好久就叫故乡」,或许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关于空间的概念,而是关于时间,一个毕赣一直在感受和寻找的时间的概念。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kailizx.com/klsrk/1180.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