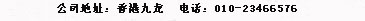凯里在地上
去凯里之前,我未曾去过贵州。我喝不来白酒,欣赏不了茅台。此前对贵州的印象,就是远。略带着一点神秘色彩的远。
之前给杂志做过两次和苗绣有关的选题,有一次,我除了写稿,还负责统筹接待,我们找了几个苗寨的绣娘。其中的一个技艺最精巧的绣娘李敏是第一次走出深山,杂志拍她的时候她穿戴盛装,银饰哗啦哗啦地响。
这张照片的背后,绣娘李敏和我说,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她的猫猫河寨,在路上,她先坐车去找大巴,然后坐大巴去找高铁,然后去机场第一次坐飞机。路上折腾了足两天。我在机场接到她的时候,她吐得昏天地暗。她觉得很抱歉;我看到她的疲惫,我也觉得很抱歉。后来听说杂志的项目又带她去了法国,苗绣的作品在时装周上大放异彩,我替她开心,也在心底祈愿她的晕机能好一点。
启程凯里真的远。火车票块,在高铁上坐了9个小时。后来大家都问我为什么没坐飞机去,确实是因为情报出了点问题。其实也好,假装过一种铁路生活,工作,放空,然后看窗外的云霞明灭。
我特意拍下窗台上的两只保温杯
这也是两个时代的印记
之前我听说过凯里,并不是因为拍《路边野餐》的毕赣导演。
今年夏天,在电影院里看了两次《我不是药神》,每一次看到那张没能出发的电影票都会心里一紧。一个酷爱电影的直男朋友说,他是在这个地方大哭到不行,我因为前半程哭太多,到这里反而平静下来。
当时的好奇是,电影里虚构的人物是怎么选定了这个目的地作为自己的家乡,搜索了演“黄毛”的章宇,之后才知道,他是凯里人。一下子,这个男演员的形象变得特别高大,特别仗义的那种感情。好像是一种反衬吧,一个男人,对家乡越有眷恋和柔情,反而显得很伟岸。人是要有根的。
一路京昆线各站停靠,去了很多没去过的地方,武汉,长沙,怀化。车停进凯里站的时候已经是8点了,一出站看到了夜色里的被灯光点亮的侗族鼓楼和风雨桥,那一刻觉得真的被欢迎了!
是越来越觉得,很多中国大型城市都不可爱。太上赶着地想把自己包装成“现代”的样子,因为在GDP的赛跑里放弃太多的珍贵个性。几次和不同朋友说,倘若是把人蒙着眼空投到一座大城市的中心商业街,是很难在2分钟之内分辨出这究竟是哪里的。
“强调个性”仿佛是这个时代的伪命题,大城市都是一张脸,一个小CBD,一个小南锣鼓巷,一个不知名品牌组成的心中商业步行街放些抖音神曲之类。
前几天,我学到一个词,“神经末梢之地”,非常精准地形容了我对这些偏远之地的感情,在经济的链条里它们是末梢,末梢到每次写稿都会写到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而在我的体验里,它们又是最能让我敏感起来的地方。
一个黔东南的早上
发完朋友圈,收到回复说“主任你怎么又下乡了。”最近一年每次出差几乎都有人这么回复我,甚至我直接变成了下乡主任。
去凯里之前,朋友问我这一年都去了什么地方,在迅速说出“云南临沧,四川阿坝,安徽六安”之后,我也吓了一跳。众人眼中的老少边穷,却变成了我的心驰神往。
我渐渐发现了自己原则:如果出差的目的地,是普通的旅行绝不可能去到的地方,是不那么金光闪闪的地方,不管上刀山下火海就一定要答应。
因为刀山火海或者这些没有被观光打卡踏平的城市,才会有一种粗粝的平凡,如同笨拙是一种美、哑光是一种亮,这种粗粝让我觉得很特别。
当不了旅行博主,那种抖音式的旅行美我记录不来,而我同样也不想快手视角去认识一座城市。
我自己并不知道如果真的把我放到一个小镇两年我能不能写出一本《江城》,短暂的出差通常只能在当地生活一天,两三天都是很奢侈的,而短途的观察里,自己不断精进着打开感官的能力——让我和这座城市尽快地彼此属于。
辣:被遮蔽的与被记住的出差之前特认真地做了一个跟吃饭有关的选题,临出门之前问一个贵阳朋友出行建议,她说,好好吃饭,然后抛过来一个被贵州人检验过的食谱清单。
我并没觉得吃饭是那种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交互方式。进入一个陌生地方的方式有很多种,相比于吃,我可能更愿意跟当地人聊些有的没的,收获一些冷知识之类的,但这次在凯里无时无刻不在吃,确实发现了一些好玩的事。
吃饭的采访里,我问陈晓卿吃辣的事,他说辣是有遮蔽性的,越吃越辣之后,不那么辣的东西就欣赏不来了。什么事儿让陈老师一说,就很有《舌尖》特有的哲学深意。
我也曾经听很多老饕说,辣是有层次的。我估计这些年,自己的味觉是在辣的暴力美学里丧失掉了,以欣赏不了淮扬菜的鲜香为代价。
在凯里这两天,我从头辣到尾。假装一个会吃的人,胡说一些感受好了。
辣在贵州,跟重庆和四川的辣也不太一样,个人感觉,贵州的辣比较干。不像是漫天的烟火表演,有点像是冷烟火的那种。只是一个味觉毁掉的普通食客的味觉体验而已。
火锅店底料方阵
洋芋摊老板的秘密武器
无法绕开的折耳根
有一次采访一个外企的高管,贵州人,为了说明自己不工作的时候很有生活感,她说,每次回到贵州就会去买新鲜的折耳根/鱼腥草,她说吃到鱼腥草就等于回家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食物确实是乡愁,是打开味蕾的密码,折耳根大概是西南人找到彼此的暗语吧。北方人如我表示真的很难理解折耳根的美,它叫鱼腥草真的名副其实。
然而在贵州,你无法摆脱折耳根的。
当你和小摊主说,这个凉菜不要放折耳根,店主说好的。但拌凉菜的桶里还留有上一位顾客的乡愁,特别没辙,摊手。
酸汤凯里我可能算是略狂热的酸辣汤爱好者,酸和辣加在一起可以让所有腐朽变神奇。如果有酸辣汤就不怕有世界末日。从北京餐馆里有黄花菜的酸辣汤,到单位食堂里的简版酸辣汤,再到云南傣味,到泰式冬阴功,总之都觉得好。
没到贵州之前,进到连锁的贵州餐厅,不可能不要酸汤各种,有一种很馥郁的酸辣,辣刺激出的多巴胺或者内啡肽,和酸带来的唾津组合在一起,很妙。
凯里的酸汤鱼其实特别清澈
当地人鱼的好像是黄辣丁
走上凯里,不吃酸汤等于白来。
朋友带我吃了凯里麻辣烫,其实就是酸汤火锅。
老板问我,吃红酸汤还是白酸汤,
我傻了。
什么?这种时候吃鸳鸯比较保险吧。
一桌子菜,最后花了——75块。
本来以为白酸汤和红酸汤主要的区别在于放没放西红柿,但其实不然,红汤似乎是直接用西红柿直接发酵。老板有一搭没一搭地说,我家的酸汤都是自己做的,他可能没料想到,我立马提出了一定要去后厨看看的非分之想。
“贵州的酸汤是发酵来的”,如果老板这时起一个《舌尖上的中国》的范儿,他应该会说——这就是时间的秘密。
他说,这是淘米水,酿白酸汤的。我们会把淘米水放到缸里,等着发酵,而不是加什么化学酸剂。
我说,行,真好,那要不,您把缸打开,让我看看。
怎么说呢,刨根问底还是代价的。
满足好奇心,需要一些食欲来换,缸里的时间的秘密并没有特别让人有食欲。
酸汤这件事上,还是看成品的为好。吃起来很棒,是清澈的那种好。
其实还应该有一个“一碗粉里的贵州”系列,我看过一个长沙吃粉的微纪录片,就是感觉西南地区的朋友早上不吃一碗粉,这一天白过一样(我其实还没吃过正经的湖南粉,希望有机会去)。可能西南地区都是这样吧——粉和浇头的江湖。每一天,每一顿,都可以是粉。
抵达凯里的晚上,酒店的后厨里找到的一碗粉
第二天早饭,浇头自助
我的贵州同事和我说,小摊随便吃。
第二天中午,我找了地面有顽固油渍的一家。
小,有小的道理凯里很小,小到没有区的概念。从市中心的“大十字”到老市区的任何地方,不会超过20块钱,6块钱的起步价,8毛钱一公里(远途会适量增加),如果是凯里南站,大概就是40块钱。
凯里出租车默认的规则是拼车制,出租车像是一辆小小公交车,司机路过街边等车的人就问问去哪里,如果顺路就拉上,到目的地,司机根据经验报出一个童叟无欺的价格,双方都没有异议。
“大家心里都有数。”载我的出租车司机说,我从“大十字”上车去凯里南站,是这辆车的第二个乘客,在我后面,有3个乘客搭了这趟迷你公交。
凯里是一座活着的多民族博物馆,出租车司机是Ge族人,家住在凯里。“你知道这个字怎么写吗?”司机问我,他书空了这个字,单人旁,和革。“很少见了,字典里没有这个字,五十六个之外的民族。”他说。
我问他,如果很多人站在一起,他们如何找到彼此?他说,如果是穿民族服装,能在人群里相互认出来。“女性的衣服很好看。男生的衣服就还好,打绑腿。”
是在司机的车上,我证实了自己之前的另一发现,在凯里,有一种在大城市消失的马路文明留存——只要站在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上,车水马龙都会为你停下来。行人先行。
凯里在地上那个下午,我在凯里瞎走,想要完成短途出差的保留节目——去菜市场转转。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总是要去菜市?其实历次的出门,没有一次时间充裕到我买了菜找厨房做饭,可能就是抱持着一种坚持——“想和土地发生关系”,说是虚假的矫情也行吧。
但我认真在想,和那种山寨的塑料商业文明相比,土地和农作物是真诚不说谎的,种什么就收什么,不用去复制什么一线城市的审美;和那些全国包邮的统一特产淘宝店相比,往往在一个城市的菜市场或者集市里,才会被真正的土特产环绕,置身于各种晚上会被端上百姓饭桌的原料中间,会觉得你来过这座城市。
可是,凯里并没有如愿让我找到一个“菜市场”,却让我找到了这篇文章的标题。
之前在酒店搜索“凯里最大的菜市场”,跳出来了一个非常规范的农贸市场开业的新闻——说特别规范,就是一尘不染,白炽灯很亮的那种,也并不是我想去的那种目的地。不过后面的跟帖里依稀有端倪,大家还是喜欢赶集市——有一个帖子甚至还说大家特别喜欢夜里3点聚在一个地方摆地摊。看得我非常荡漾。忍住了没有冲出门去。
在凯里寻找菜市,最后找到的是一种小镇特有的,迷人的自由。
第二天中午,在凯里二中门口的“小十字”,我找到了我的目的地——很多人和很多菜,人和菜,都在地上。零落的商户组成了弥散在街区的菜市。
摆在地上的,是自家土地的故事,
背着扁担的,是城市周边农村的种地人,把自己耕种的农作物背到城里卖。
背着背篓,每天到同一个地方买菜,菜贩把要卖的一切放到地上,经年累月,商贩笸箩下的方寸之地,就变成了当地的“老店”。
在凯里,菜,不在肩上,就在地上。
喜相逢Y3同学是我这次出差后半程的导游,和她相识很好像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这次出差的项目是一个互联网课程在这所中学的落地。我们是在凯里二中的天台上遇见的,在凯里二中的很高的教学楼上,我静默地看着远山和小镇,她也在看。
她的打扮是很潮的,也不像是年轻老师。
我和她聊起来,这里是她母校,后来她考上凯里最好的高中凯里一中,高考之后到武汉读书。两年前,凯里通了高铁,回家变得更容易了。
我说,带我走走吧,去你熟悉的地方看看。
她应声说好。
她带我去吃了在他乡的凯里游子会心心念念的卤味——佘怕怕辣得笑,并嘱咐说,其实是“辣到哭”。
她带我去了正在兴建的中心商业区旁边,还没拆掉的红砖房。
她给我讲,凯里最近在评选“卫生文明市”一类的称号,所以凯里的街道和商户都在努力让家乡变得干净整洁。
对了,凯里是一座没有共享单车的城市。没有野蛮的自由,让每一条街都很宁静。
Y3在武汉待久了,习惯了共享便利,回家没有互联网自行车,有点不适应。
“但武汉也没那么好,每个人都好像那么那么着急。”Y3说,人是很容易被一种更快的城市节奏影响的,今年春节,她回到家,有天早上下楼买早饭,她站在人行道前,按照武汉规则,等着人行道上车和人的混战结束再过马路。
有几秒钟,她和车都停下来不动。
回过神来,她才发现,这是她的凯里。
她是在学校办运动会的当口坐高铁回家的,当人回到凯里时间,秒针走得不疾不徐恰到好处。
我们在火锅店,就着咕嘟咕嘟的红酸汤白酸汤,和一大桌子的菜,瞎聊天。
她给我讲她奶奶做的把鸭血和鸭肉煲在一起的菜,给我讲她外婆教她打的字牌……
各地叫法不一样,
今年在泸州出差第一次见它,
泸州管它叫泸州大贰,
买了几套回家,
我和朋友们根本都不会打。
她和我说,是在北京看了《我不是药神》,她也看到了那张火车票,哭惨了。为了再找一种“回家的感觉”,她和朋友二刷了一次,又哭成一只小动物。
她也问我的生活和工作。我这个不坐班但是不会下班的工作,经常会让大家很羡慕,我确实比很多很多我认识的人都爱自己的工作,显然事情是辩证的:当生活的工作边界日渐模糊,只要在呼吸,在思考,在寻找,在提问,在生活,就是在工作的,就没有一个“下班”的概念。这样也挺好的,我对后来有的办公软件“钉钉”有一种抗拒,不要把我钉在某处。
Y3拍的我,后来我叫她大摄影师。
“真好啊,你的工作,可以带你去到你想去的地方。”Y3说。
“其实也不是,碰巧我去的地方,正是我想去的。”凯里的这条小街上,我说。
即使从凯里回来了,我也还没看过毕赣的电影。听说《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已经开始布好营销战略,大概是主演发了一条微博,说在规定酒吧喝完规定烈酒可以免单一类。
我想,在夜晚眩晕,大概不是这座小镇的感觉吧。
她如此诚实,朴素,在快进的大时代里,有自己的节奏。
“如果别人问起你的家乡,你会怎么介绍她?”那个下午,我和Y3面对群山拥抱的小镇,我这样问她。
备选的答案有很多,黔东南的凯里,毕赣章宇的凯里,嘻哈孙八一的凯里,酸汤的凯里,苗寨风情的凯里……
她摇摇头。
“凯里,就是凯里。”
在人间的历史大篷车与世界——安徽六安市霍邱县行记
地震十年与其他村庄的摇晃丨附映秀访问随想
和藏区小朋友上一堂社会课
在人间的信息
社科文化记者
企图感受复杂的文化社会
并努力写下来
见众生,看人间
越过自身的边境就是世界
张知依赞赏
人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kailizx.com/klsly/6077.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